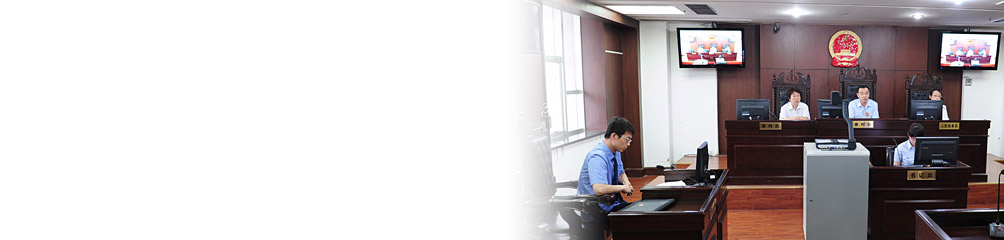一、问题的提出
A公司与B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法院经审理,判令B公司将租赁设备返还A公司。因B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A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因租赁设备已毁损,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C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如下:(1)因租赁设备已毁损,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由B公司折价赔偿A公司100万元整,上述款项B公司承诺在2013年3月31日前给付;(2)案外人C自愿为上述债务的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B公司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履行,2013年4月,A公司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并追加C为本案被执行人。
该案审查过程中,就是否应当追加C为被执行人并追究其保证责任,执行法院形成如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追加C为本案被执行人,责令其在1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1)本案中,B公司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未按约履行。法院应当依照A公司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2)C在和解协议签订过程中自愿提供担保。据此,在被执行人B公司未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法院有权裁定追加担保人C为本案被执行人并责令其在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不得依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径行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如申请执行人要求追究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应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执行和解协议另行诉讼。理由如下:(1)依《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被执行人未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仅可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执行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力,人民法院不能径行依照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裁定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并履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2)执行和解协议虽无强制执行力,但其本质仍属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具有私法上拘束力。应当允许申请执行人持执行和解协议另行诉讼。
本案的处理涉及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执行担保条款的效力及执行和解协议可诉性等一系列问题的审查认定,笔者在下文中逐一探讨。
二、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
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但是,法律就执行和解协议本身的效力,却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目前理论界对此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和解协议类似于实践性合同,其效力存在于履行完毕之后,还有人称其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即以协议内容的完全适当履行作为生效条件,依照该种观点,执行和解协议甚至不具备最基本的私法上的契约效力;第二种观点认为和解协议是民事合同的一种,理应具有可诉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对审查确认合法有效的执行和解协议,应当确认其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尽管基于执行实践的需要,理论和实务界关于在一定条件下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如果执行机构能够像在诉讼调解中那样,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那和解协议将具有公法性质,从而具有执行力。而如果和解协议具有了执行力,则意味着执行程序能够改变生效裁判的内容,审判与执行分立的基本司法体制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基于上述理由,立法机关对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一直未予明确认可。因此,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因执行和解协议本身并非法定执行依据,人民法院不得依该协议对债务人强制执行。
三、执行担保条款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31条确立了强制执行法上的执行担保制度。据此,构成执行担保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被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2)该担保应当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因为现行法律对执行担保制度的规定较为简约,实践中对执行担保的效力问题争议较大。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分两种情况对执行实践中执行担保的效力问题进行分析:
(一)被执行人向执行法院提供执行担保时,双方当事人未签订执行和解协议
上述情况下,因双方当事人未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故不存在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方式等情形,可称为纯粹的执行担保。于此情形下,如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法院可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此点应无争议。
(二)被执行人提供执行担保时,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
基于法律明文规定了执行担保需经申请执行人同意这一要件,实践中,执行担保的提出往往与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相互关联,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1.双方当事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担保人为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向执行法院提供担保。于此情况下,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直接指向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因此,当被执行人未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时,可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担保人的财产。
2.双方当事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担保人为和解协议的履行提供担保。本文讨论的案例即属该情形。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的担保已经不能认定为严格意义上的执行担保,如被执行人未按照和解协议履行,执行法院不得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理由如下:首先,依照法律规定,执行担保应当向执行法院提出,而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是向申请执行人提出的,不符合执行担保的构成要件。其次,执行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并无公权力的介入。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因执行和解协议并非法定的执行依据,在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执行法院仅能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而无权在执行程序中对涉及双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执行和解协议及担保条款予以审查,并据此追究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第三,执行和解协议通常都会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进行变更,而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是为了担保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而签订的。因此,如果执行法院径行依照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要求担保人履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显然与担保人提供担保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相悖。
四、执行和解协议可诉性
执行和解协议虽无强制执行力,但并不妨碍申请执行人持执行和解协议另行诉讼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理由如下:首先,《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在被执行人未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但并未排除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其次,执行和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就变更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系私法自治原则在执行程序中的体现,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的,为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对方当事人当然可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另行诉讼;第三,根据既判力理论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确定判决对诉讼标的所作判断具有确定力,禁止后诉法院作出与前诉法院生效判决内容相悖的裁判,禁止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诉讼。但是,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事实发生在原法律文书已经生效后,执行和解过程中,基于原诉产生了权利的减让、变更、补充等事实,诉的标的、主体、原因均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产生了新的、非原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所能涵盖的法律关系。据此,一方当事人持执行和解协议另行诉讼并不违反既判力理论和一事不再理原则;最后,就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对个案的答复中已经开始明确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诉性。
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及效力认定问题涉及实体法与程序法,审判权与执行权的融汇缠绕,交错重叠,立法机关基于维持生效判决既判力和审执分立体制等因素的考虑,未赋予执行和解协议以执行力,应当说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但是,通过法律解释来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可诉性,既维护了诚实守信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照顾了审执分立的司法体制,体现了法律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尊重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维护,不失为解决执行和解协议相关争议的一条良策。